失落的藝術:研究作為消遣
業餘研究者究竟去了哪裡,我們又該如何讓他們回歸?
原文:https://kasurian.com/p/research-as-leisure
作者:Mariam Mahmoud
譯者:Kurt 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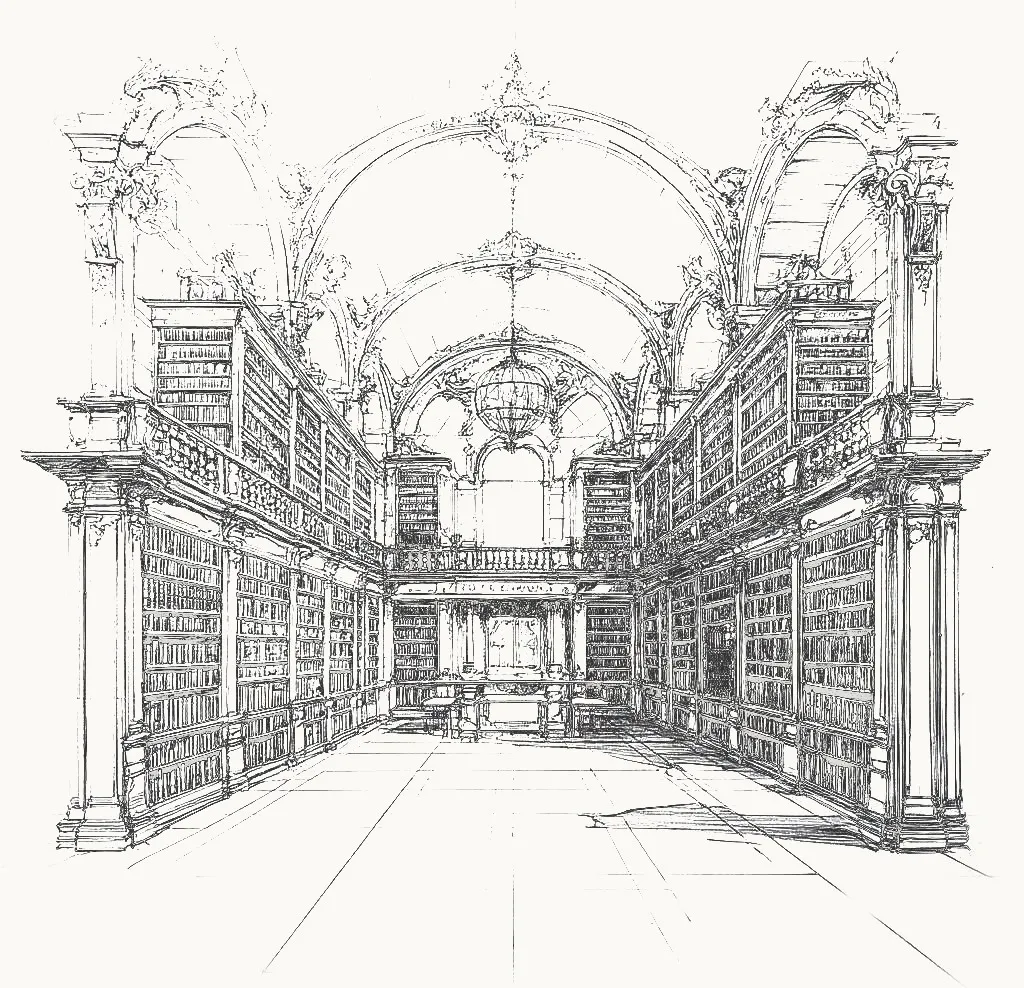
文明的文學基礎
坐落於舊金山福特梅森的一處結合咖啡館、酒吧、博物館與活動空間的場所中,有一座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圖書館,珍藏著長今基金會的《文明手冊》。這是一套大眾精選的藏書,共收錄3,500本對維繫或重建文明至關重要的書籍。《文明手冊》源自一個問題:若你被困於一座孤島(或一顆環境不利的小型星球),你會選擇攜帶哪些書籍?
這套藏書展示在充滿工業感的牆面上,既莊嚴又充滿希望,既真摯又略顯徒勞,彷彿浪漫主義者心中的書卷金唱片。最生動地說,它是一座令人謙卑的紀念碑,見證了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所宣示的「書籍是文明的載體」這一真理。塔克曼曾寫道:「若無書籍,文明的發展將無法實現。」
將文明與人類文化聯繫於書籍、閱讀與寫作的觀點,並非僅屬於塔克曼一人。
近350年前,加利略便宣稱書籍是「人類所有令人讚嘆發明的印記」,因為書籍使我們能跨越時空溝通,與那些「尚未誕生,或千年萬年後亦不會誕生的人」對話。
幾代人之後,亨利·戴維·梭羅在瓦爾登湖的隱居中寫道:「書籍乃田野間珍貴的財富,是世代與文化應得的傳承。」
隨後的一代,卡爾·薩根在帶領電視觀眾穿越宇宙之旅後,獨自漫步於圖書館,重溫加利略的見解。當航海者二號金唱片中那首漂浮的貝多芬樂曲《卡瓦蒂娜》響起時,薩根驚嘆於書籍的存在。他說:「寫作也許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它將彼此素未謀面、來自遙遠時代的民眾緊密聯結在一起。」他最後總結道:「一本書,就是證明人類能夠創造奇蹟的證據。」
塔克曼的這句老生常談,便在數個世紀中持續流傳:書籍承載著文明。這並非因為書籍本身蘊含著神聖不可侵犯的知識,而是因為閱讀與寫作構築並塑造了文化;而若無文化,便無文明。
神聖的閱讀命令
在阿拉伯語中,文明的根字 ح-ض-ر(意指「在場」、「定居」、「停留」)展現出從漂泊到定居的深刻轉變。對伊斯蘭而言,這一轉變始於在城市與沙漠交界的探求。
1450年前,一位追尋靈性居所的遊子在2000英尺高處俯視著克爾白,距離超過兩英里,他接到一個命令:閱讀。先知穆罕默德 ﷺ回答說:「我不懂閱讀。」命令再次下達:閱讀。聖先知再度回答:「我不懂閱讀。」命令再度來臨:「以創造者之名閱讀。」
關於伊斯蘭起源的故事,已有太多論述——這故事透過人類最嚴謹而精密的口頭傳承系統被保存下來——以至於在一篇論及閱讀的文章中,人們都會猶豫是否引用它。然則,正是藉由這一神聖的命令,亞伯拉罕、摩西與耶穌的神開啟了伊斯蘭文明的歷程。以創造者之名閱讀。
獨處與社群之間
命令一個不識字的人閱讀,顛覆了將閱讀僅僅視為解碼印刷符號這一單一觀念。阿拉伯語中的「Iqra」常被譯作「閱讀」,但其實同時蘊含著「朗誦」的意涵。朗誦是一種主要透過口語、外向表達的行為,而閱讀則是一種更私密、獨處且內省的活動。
伊斯蘭起始經文中的「閱讀」體現了正如艾倫·雅各布斯在《分心時代的閱讀樂趣》中簡潔所言,『在孤獨邂逅與更具社交性的互動之間不斷轉換』。在現代閱讀的語境中,「社交」可以呈現為任何形式——日記、部落格文章、讀書會、文學沙龍、一場端莊的線上辯論,甚至是一封致友人的信——因為正如雅各布斯所寫,「每一個偉大理念的實現,都是連結與沉思交織、在兩者間來回穿梭的成果」。
如果閱讀未能向外延展,構建並貢獻於那生生不息的人類知識網絡,那神聖的閱讀命令便顯得受阻、無法達成其使命。
然而,僅僅依賴閱讀——即便其兼具雙重性——仍不足夠。古蘭經中閱讀的命令具有明確的方向性:
以創造者之名閱讀。祂從一團黏稠之物中創造了人類。閱讀吧!你的主乃是最慷慨者,祂以筆教導,傳授給人類那些他們所不知的知識。
以我們創造者之名閱讀的命令,正如Rebecca Elson在詩作《我們這些天文學家》中所言(該詩表達了對幻滅的抗拒),賦予了一種「令人敬畏的責任」。古蘭經中的「閱讀」可被解讀為一種令人敬畏的責任,一個既要求嚴謹探究,又呼喚虛心驚奇的學習邀請。
最後一位閱讀者的漫長世紀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這項我們敬畏的責任成為了一種焦慮的來源。
1926年——那一年,無線電這項令人目眩的新發明走入美國家庭,將世界連續劇帶進全國的客廳;那一年,貝爾電話實現了從紐約到舊金山的橫貫通話,只需18美元;那一年,奧菲姆劇院在洛杉磯開幕,其傳奇的霓虹招牌至今仍熠熠生輝——弗吉尼亞·伍爾夫開始憂心閱讀的未來。在1926年8月3日出版的《新共和國》中,伍爾夫在比較電影與閱讀時,對電影的恐怖感到不安甚至近乎厭惡。她寫道,電影以及我們從中獲得的快感,源自一種過於粗糙、背離文明的人性衝動。這位典型的沉思樂觀主義者曾於1915年1月著名地寫道:「我認為,未來是黑暗的,這是未來能有的最好狀態。」雖然她並未直接譴責閱讀的未來,但她認為影音媒介正危險地侵蝕著深度。
25年後的1951年——那一年《我愛露西》首播,用木製電視盒取代了家庭無線電;那一年有反美調查委員會;那一年內華達沙漠進行了首次核試;那也是1952年科技彩色影像消逝前的最後一年——深受喜愛的兒童文學作家E.B. White(《夏綠蒂的網》和《小斯圖爾特》作者)對閱讀的未來感到憂心。在《紐約客》「鎮上之談」專欄中,White回顧了羅林斯學院院長的預測:「五十年後,全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會閱讀。」White寫道:「在我們看來,即便在每一億五千萬人中僅有一人繼續成為閱讀者,他也將成為值得挽救的人,是建立大學的核心。這位『不可能的人』,這位『最後的閱讀者』,便是那『蜂后』,從他身上衍生出『與久遠過去透過斷裂的智慧鏈條完美聯繫的新一代人,以延續社群。』」他最後斷言,更有可能的是,人類將透過影音設備延續下去,那些設備不要求心智的自律,且已令空間彌漫著鴉片館般的慵懶感。
45年後的1996年——那一年,福克斯新聞在衛星電視上首播;那一年,多莉羊複製成功;那一年出現了「微型電話」,撥號上網、「滑鼠」與「鍵盤」、『www』和『@』齊現;也是亞馬遜改變互聯網的前夕——蘇珊·桑塔格開始憂慮閱讀的未來。
她在致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一封信中(距博爾赫斯去世十年後)向這位老友致歉說:「很遺憾告訴你,如今書籍已被視為瀕危物種。」她所指的不僅僅是書本本身,而是「構成文學及其靈魂效應的閱讀條件」。不久之後,「我們將隨需召喚『書屏』,任何『文本』都能被調用,並能改變其外觀、向其提問、與之『互動』。」桑塔格的結論呼應了White與伍爾夫數十年前的憂慮:當書籍變成我們「互動」的「文本」時,書面文字將僅僅成為我們那由廣告驅動的電視現實中的另一面向;這不僅意味著書籍的消逝,更等同於內心世界的死亡。
近百年來——每一年,未來似乎都比我們能處理的速度更快——我們一直憂心閱讀的未來。然而,無論是這些作家,還是哈羅德·布魯姆在《如何閱讀與為何閱讀》、莫提默·J. 阿德勒與查爾斯·范多倫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以及尼爾·波斯特曼在《娛樂至死》中的預言,都未曾預見到這樣一個未來:一個介於「口語性」與「讀寫性」之間的詭異空谷,周圍雖充斥著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多的書籍、文字、閱讀與寫作,卻缺乏連貫的文化。
伍爾夫、White與桑塔格預見了影音媒介對人腦與靈魂的腐蝕性、野蠻影響。他們憂慮的並非書籍的消逝,而是當閱讀從一種全神貫注、沉思的行為轉變為被動、碎片化、表面化的狀態時,將導致文化崩壞。閱讀的死亡,不是書籍的消失,而是文化的失落。
文化危機
這些恐懼並非毫無根據。今日,我們正處於伍爾夫、White與桑塔格所預見的那種文化危機中——並非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而是一個碎片化注意力與表面性參與侵蝕了共享意義與文化連貫性基礎的世界。
「文化」的定義就如同其所要描述的現象般流動。在《王子與權力》中,詹姆斯·鮑德溫指出,只有處於危機中的文化才會要求界定「文化」的意義。
我們正處於一個文化危機之中。正如韓炳哲在《儀式的消逝》中所闡述,我們缺乏賦予意義的結構與形式,這導致了文化的碎片化,其結果便是文明式的ADHD——一種世代性的躁動、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無目的的過度移動,使得洞察變得難以捉摸且稍縱即逝。
研究作為消遣:艾略特與皮珀談文化復興
對於T.S.艾略特而言,在二戰後的英國,「文化」是一個互相依賴的三層次感受——個體、群體與社會——共同構成了「整體社會的格局」。若任一層次與其他層次脫節,無論是個體與群體,或群體與社會的分裂,「更高的文明便難以尋獲」。
在這片碎裂的景觀中,我們所需的不僅是診斷,更需要處方。當我們的注意力方式受到侵蝕時,如何重建文化的基礎?答案或許在於回歸對消遣的古老理解——消遣不是懶散,而是一種有導向的沉思。
尤瑟夫·皮柏在與艾略特同時代的背景下,於一個滿目瘡痍、四分五裂的德國中宣稱,消遣乃文化的基石。對於「消遣」,皮珀並非指懶散,而是更古老意義上的消遣——即希臘語中的 σχολή(學院或學校)。
皮珀所說的消遣是一種沉思式的狀態,本質上是一種無拘無束的研究風格。這樣的消遣不僅僅是為了知識本身而追求,也不僅是純粹的「為樂而讀」。構成文化基礎的消遣是一種有導向且刻意的好奇心——它是以充滿驚奇而非僵硬確定性的態度提出問題、尋求答案的實踐。若閒暇時間未用於研究,未用來提出問題並以探險者的精神探究答案,文化的連貫性便會瓦解。對皮珀而言,若缺乏以書信為基礎的消遣,或所謂的「研究作為消遣」,就無法構築出更高文明所依托的格局。
總而言之,艾略特與皮珀提供了互補的文化架構:艾略特描繪了文化的外在格局,而皮珀則描述了滋養並重塑這一格局的內在狀態——消遣。缺乏艾略特所描述的結構連貫性,文化將面臨瓦解;缺乏皮珀所推崇的沉思式消遣,這一結構將變得空洞。
以書信為消遣,將閱讀與寫作重新定義為既充滿趣味又深思熟慮的活動,讓驚奇、好奇與發現的喜悅得以正式呈現。它之所以成為文化的基礎,是因為透過思想的交流——無論是當代作家還是千年前的文人——社會的格局得以被組織、重組。
凝視著那詭異空谷的深淵,「以書信為消遣」開啟了一種全新的文化想像;那種既正式又充滿趣味、由刻意好奇驅動的思想交流,孕育出一種新文化。
反對空洞閱讀
文化復興在實踐中該如何展現?重組整體社會格局始於觀念上的轉變:將閱讀與探究視為一種充滿趣味且有意識的好奇行為,而非繁重或僅限於學術範疇的行動。
對某些人而言,閱讀的衝動表現為一種生產力技巧,或是被動地消費那些流行的自助書籍與小說;這些讀者不把閱讀當作洞察周遭現實的工具,而僅視其為彰顯生產力美德的責任,或僅僅作為娛樂,與真人秀節目無異。
而對許多貪婪的讀者來說,閱讀的衝動則演變成一種確認偏誤:收集那些能印證既有世界觀的觀點碎片。這些讀者將閱讀視作一個表面上採納與自己現有信念相符的概念的機會,而非深入探究的邀請,最終導致一種智識上的腹語現象,扼殺了好奇心。
與這種空洞的閱讀方式對立的是「研究作為消遣」——這是一種對以創造者之名的閱讀命令的莊嚴回應。它邀請我們懷著目的與好奇心審視構成生命的一切,以一種無限開放且虔誠面對神秘的態度追求知識。簡而言之,就是成為一個學生,即便我們在「知識經濟」的工作中進進出出,即便缺乏學院提供的保護與指導。
對學術界而言,「研究」是一個專業術語,但對我們而言,研究並非高高在上的學術活動,而是一項根植於人性的冒險、一門工藝、一種凝聚文化的歡聚。
非專家也能而且應該追求專業知識。
從理論到實踐:研究作為消遣之架構
1. 培養好奇心
隨身攜帶著亞歷山大圖書館般的知識資源,反而使我們的感官變得鈍化,而非敏銳。儘管前所未有地獲得資訊,我們卻流露出一種遲鈍的無好奇心,將自己交給那些推送資訊的演算法,而非主動探索。
然而,好奇心本質上是簡單的:它是觀察、專注,以及不斷追問「為什麼」與「如何」。好奇心意味著在寧靜的順服中站在創造者面前,因為每一個問題中都蘊藏著無數更多的問題。
培養好奇心就像隨手拿起一本雜誌,偶然讀到一篇關於鳥類遷徙的文章,並由此激起了進一步探索的慾望。它也像在散步時,注意到腳下的人行道或街道、周遭的建築、樹木以及動植物,並好奇這一切是如何、又為何會存在。
正是在我散步的時候,我開始對周遭的郊區景觀產生疑問:這些房屋是如何建造出來的?為何選擇這些房屋,採用這種風格,街道又為何如此寬闊?這個社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起初所見的單調蔓延,竟轉變成一個神秘的謎題,一場探索城市規劃、建築、土地使用、經濟與科技如何影響我生活的探險。
2. 提出問題
無方向的好奇僅僅是分心。對我們而言,好奇心必須凝結成一個問題。被動的好奇必須轉化為對真理的積極探索。對於研究作為消遣之人,提出問題本身充滿趣味,因為這不受學科限制、多元交叉,且不拘泥於那些晦澀難懂的學術規則。
沒有問題是愚蠢的,但大多數問題可能是糟糕的,這本身並非壞事。問題糟糕正是一個令人愉悅的過程,因為它能讓思想與聯繫隨時間漸次綻放。即使是個糟糕的問題,也依然是一個起點。
最初,我對郊區的疑問既廣泛又模糊——從「郊區是如何形成的?」到「分區政策如何創造了現代郊區?」、再到「分區的歷史是什麼?」、以及「購物中心又如何塑造現代郊區?」、「為何會有最低停車位要求?」與「郊區是否真具合理性?」……問題層出不窮。
透過實踐,我學到了一個簡單的公式:一個好的問題既要足夠具體以引導研究,又要足夠開放以促進發現。發現對於思想的綻放至關重要,因為正是在那裡,跨學科的連結和新問題得以湧現。
3. 收集證據
一旦問題成形,就需要實質內容來豐富它,而收集證據往往是研究者遇到的最大瓶頸。
首先,我們的信息生態系統使我們成為了資料的收集者,而非真正的讀者。收集PDF、書籍以及書單固然令人興奮,但也可能成為束縛,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組織這些資料。
其次,對於以研究為樂的人,自學必須涵蓋該學科的基礎經典。理解這些經典以及它們如何塑造我們對該主題的看法至關重要,因為在那裡,一種健康的異議與懷疑精神才能茁壯成長。透過理解支配一個學科思維的規則,研究者便能深思熟慮地質疑、探究傳統智慧所忽略的路徑,並發展全新的答案。
最後,總有更多值得閱讀的內容——這當然無妨。
4. 形成答案
研究必須有一個結論,即使這結論意味著引出更多待解的問題。這個結論不必驚天動地,但必須以切實的形式呈現出來,不論是一篇文章、一個影片、一個社群媒體串,甚至是一封致友人的信。
區分「研究作為消遣」與無所事事瀏覽的關鍵,正在於這種朝向創造的行動;無論成果多麼樸實,你的答案必須能促進對話,而非僅僅消費或重複他人的觀點。
5. 知識共同體
理想情況下,就如同古蘭經中「閱讀」的雙重意涵,研究的最終成果應具備社會性、對話性與共融性。研究作為消遣的藝術在於建立正式與非正式的「知識共同體」,在其中深入探討的觀點以書面形式傳遞,並呈現給更廣泛的討論。
如今,這些共同體無處不在:Substack、YouTube、Discord、Twitter;小型讀書會、寫作圈,以及全球各地客廳與咖啡館中的非正式討論小組。透過這些共同體,就如同布魯姆斯伯里小組、因克林斯、格特魯德·斯坦因的沙龍或維也納圈子,我們培養出那生機勃勃的網絡,讓思想得以檢驗、提煉、交叉激盪並傳承。
藉此,我們逐步重組出促成高層文化與文明可能的整體社會格局。
重組文明的格局
《文明手冊》提醒我們,書籍不僅是資訊的存放處,更是文化記憶與能動性的載體。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以創造者之名閱讀的神聖命令,煥發出前所未有的迫切感。
Kasurian是一個邀請,鼓勵大家走上研究作為消遣的道路;任何人都可以進行嚴肅的研究,而成為專家的門檻從未如此之低。成為你所著迷領域的業餘專家,通過電子報、論文、討論小組或參與線上論壇來貢獻你的研究,讓社群檢驗、挑戰並完善你的結論。藉由擁抱正式與非正式專業知識的文化,以及研究作為消遣的文化,我們便能重拾那份驚奇感,恢復啟發、協商並超越當下正統觀念的能力。
進一步閱讀:
Lost in Thought: The Hidden Pleasures of an Intellectual Life – Zena Hitz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the Age of Distraction – Alan Jacobs
Slow Reading in a Hurried Age – David Mikics
A History of Reading – Alberto Manguel
Notes Toward a Definition of Culture – T.S. Eliot
Princes and Powers – James Baldwin
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 – Josef Pieper
The Disappearance of Rituals – Byung-Chul Han
How Romantics and Victorians Organized Information – Jillian M. Hess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Ptolemaic and Copernican – Galileo Galilei
How to Read a Book – Mortimer J. Adler and Charles Van Dore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 Neil Postman
Technopoly – Neil Postman
How to Read and Why – Harold Bloom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 Harold Bloom
The Study: The Inner Life of Renaissance Libraries – Andrew Hui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 C Wright Mills
Tools for Conviviality – Ivan Illich
How to Write a Thesis – Umberto Eco
Dust Tracks on a Road (Chapter 10) – Zora Neale Hurston